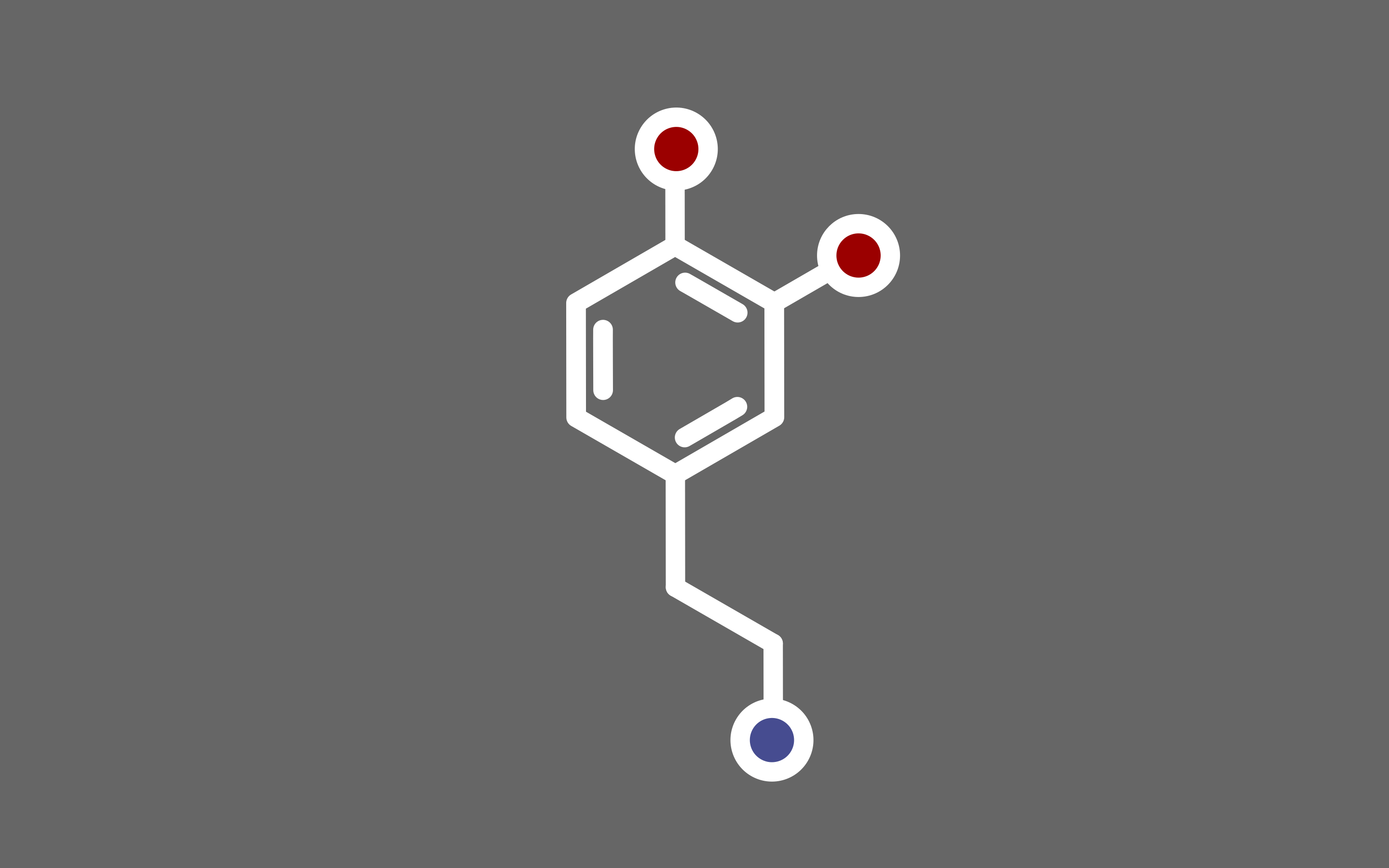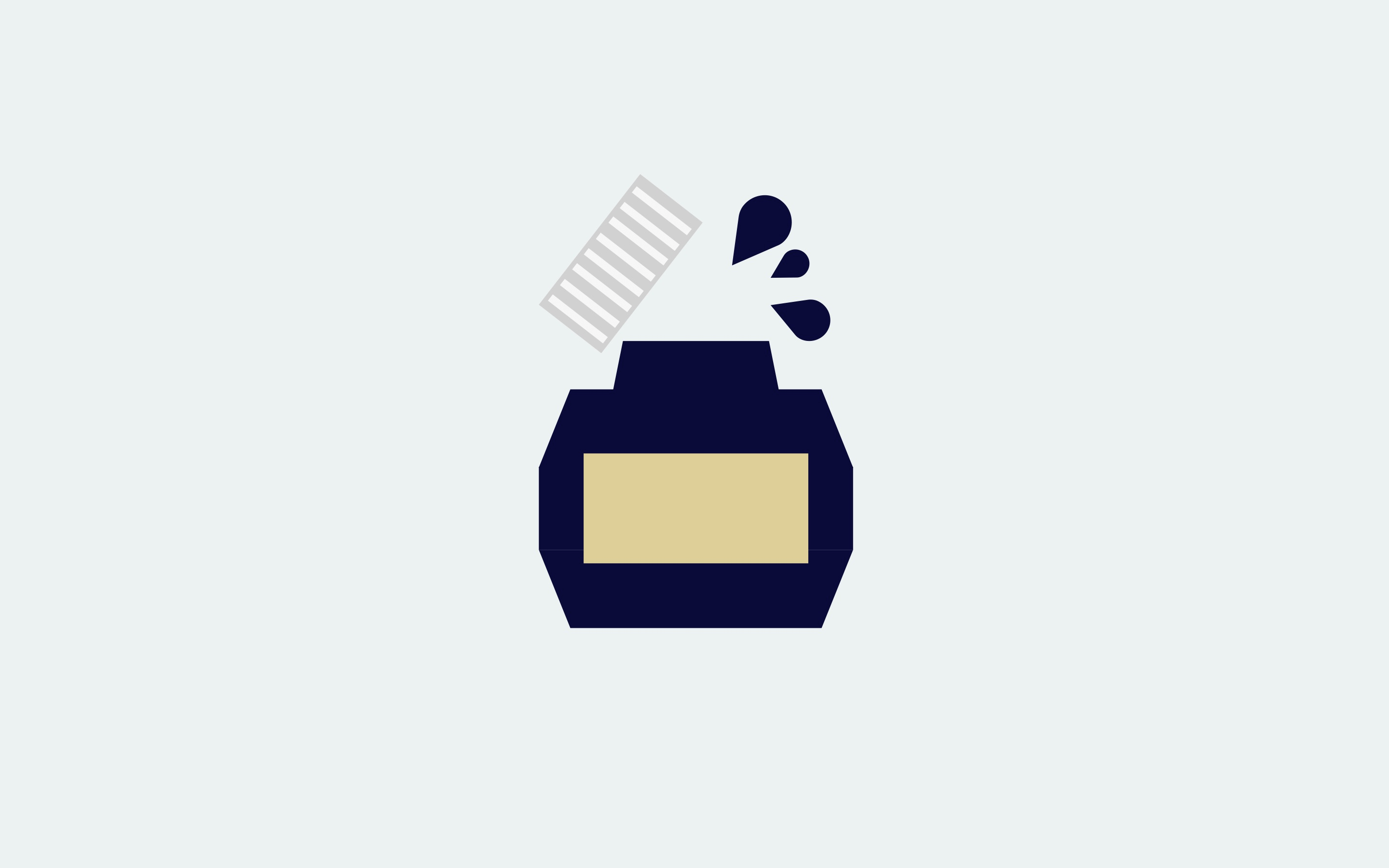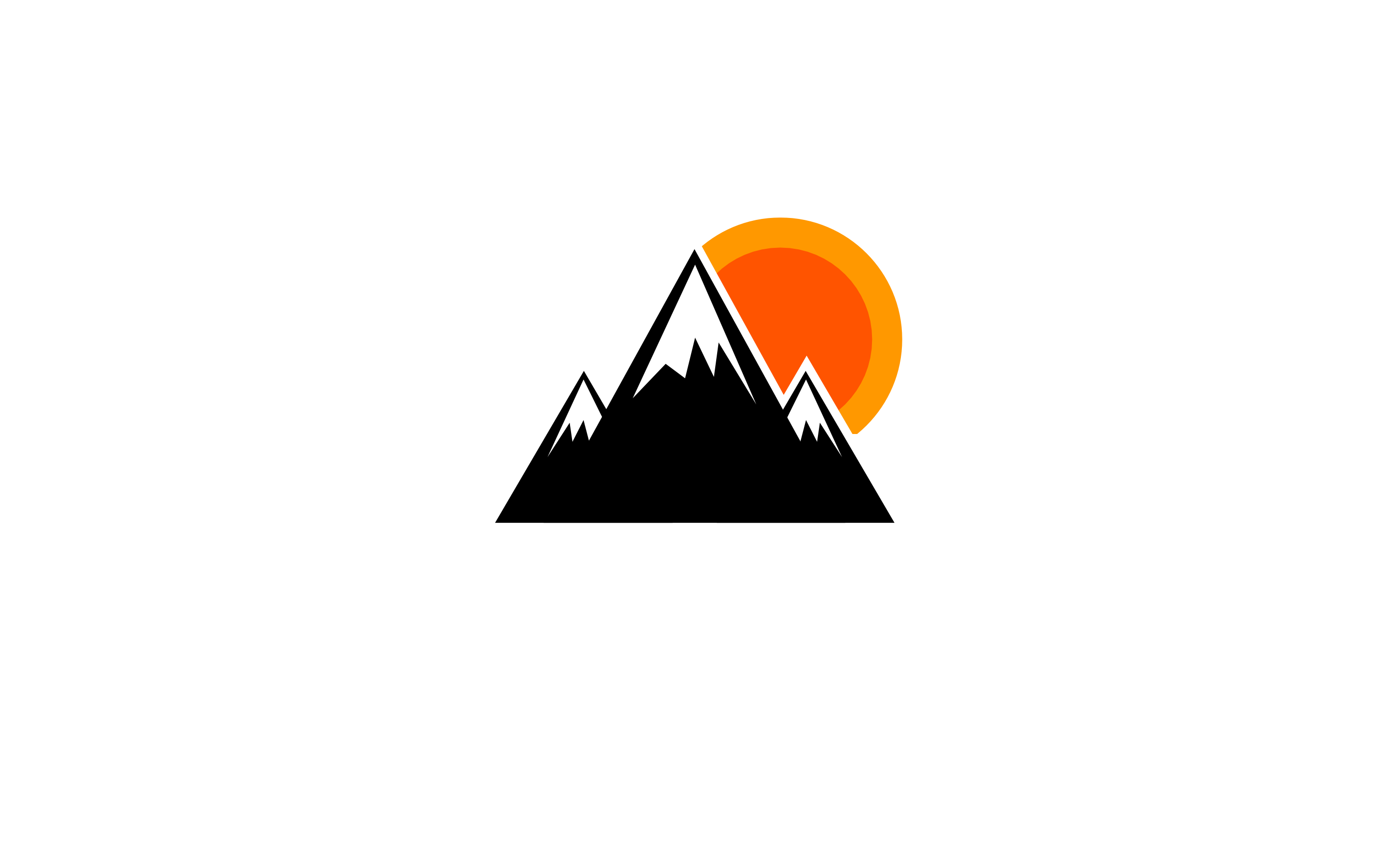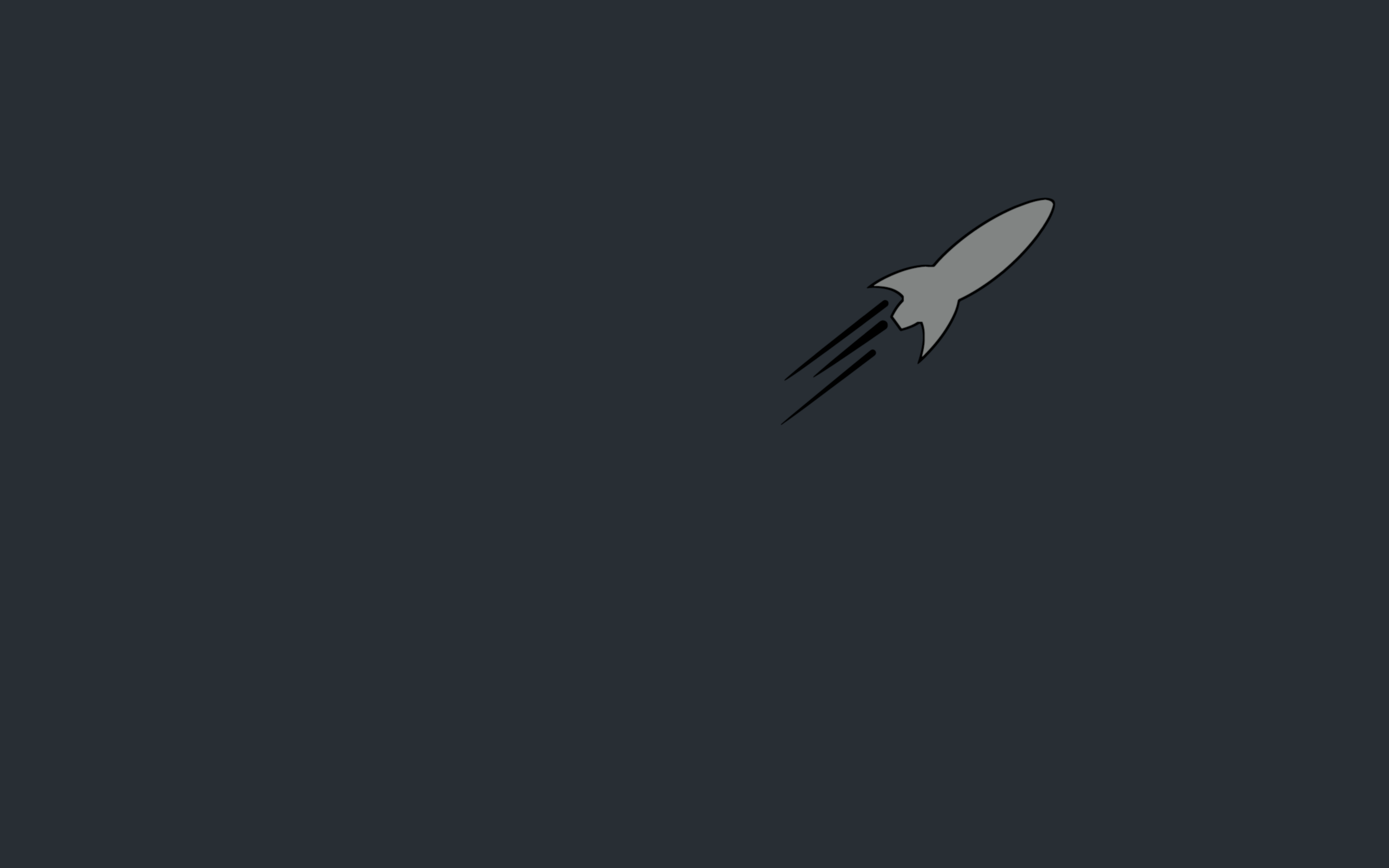理性的边界
披着科幻外衣的哲学拷问
缸中之脑描述了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把一个脑子取下来放在一个鱼缸里,用计算机模拟感知觉的输入,甚至通过某种技术为它植入虚假的记忆或情感。这个脑子能否感知自己正处在某种虚拟现实之中?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最棘手的地方在于,Putnam实际上是为一种哲学终极疑问套上了一个科幻外壳。它在事实上拷问每一个读者: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缸中之脑实际上给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答案:我们什么都不是,既不从哪里来,也不到哪里去。我们所知的世界不过是一种光影的幻象,毫无真实可言,充满了虚无主义的荒诞不经,周遭的一切都是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构建的深渊。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游戏引擎里徒劳无用的努力;快乐与痛苦,亦不过是程序虚构的假象;高尚或卑劣,在代码层面并无贵贱之分。缸中之脑要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它甚至不在意这世界上是否真正存在这样一个神奇的鱼缸,只要在理智的头脑里种下怀疑的种子,缸中之脑就自然诞生,并再不可能在理性的世界里抹去。
从缸中之脑里引出的更深刻的问题是:假如这一切不过都是幻影,我们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假如人生真如叔本华所言,不过是如同钟摆一样在痛苦和无聊中摆荡,我们为什么不干脆在电子世界里自我毁灭?正如Camus所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先辈对缸中之脑的驳斥
很多人试图解决这个缸中之脑的问题,Descartes对这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这个问题的祖先)实际上做出了很精彩的论述:感官已不可依赖,因为它们有可能是某个邪恶妖精骗人的戏法。在欺诈的世界里,只有怀疑本身不可撼动。因此,产生怀疑的主体必然存在,因为存在必然先于意识,是谓“我思故我在”;而构建“我”的必然另有其人,因此Descartes在他的形而上学第二原理中引入了上帝。上帝创造了“我”,也创造了周遭的世界,因此驳斥了缸中之脑。
Putnam从另外一个角度驳斥缸中之脑:他断言一个缸中之脑必不能设想一个缸中之脑,因为它无法构建出一个对它而言“不存在”的东西。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角度来看,存在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对存在而言,它永生不灭,亦不能被争辩,存在就是以这种方式充填整个宇宙,只有存在的事物才有可能被思考。对于不存在的事物,例如“五彩斑斓的黑”,我们无法想象它是什么,自然也并不存在;当我们以语言清晰表达出“缸中之脑”这个意项的时候,就已经跳出缸中之脑的范畴了。因此缸中之脑事实上是自我矛盾的,在说出缸中之脑并意有所指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缸中之脑了。
常识实在论者对缸中之脑提出了另一个更粗暴的解决方案:对缸中之脑理念的过分纠缠恰恰陷入怀疑论者精心设置的陷阱。仅凭常识就足以论断,现实世界存在,而无需纠结这种荒诞的幻想。Wittgenstein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演绎,他指出现实世界存在是生活实践中的框架性命题,是先于其他哲学讨论的。他并不断言这种框架性命题一定正确,但这种框架乃是实践得出的结果,而脱离实际的空想是不值得辩驳的。
然而,在我看来,上述论点事实上是等价的:无论是Descartes的“上帝”,Putnam和巴门尼德的“存在”,抑或是摩尔的“经验”,以及Wittgenstein的“框架”,他们都试图在讨论中引入某种超验的存在,而这种超验是无法被驳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Wittgenstein的“框架”与Descartes的“上帝”并无不同,它们不能被怀疑,不能被推翻,对Wittgenstein们而言,他们甚至不屑于讨论有关框架性命题,并认为这是在生活实践中不言自明的。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作弊,在无法解决怀疑论者诘难的情况下引入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推翻理性的讨论多少带点强词夺理。
我的观点
必须提前说明的是,(由于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与自然科学系统相关的)下述的哲学观点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科学系统的影响,我也主观上更推崇从科学实践或数理逻辑推导出来的理念。在我看来,原教旨主义的哲学思想最大的问题是难以被证伪和证实,他们会发明很多抽象的名词,但很多都流于空想和断言。从数学出发的观点,至少我们可以保证结论在某种弱化或约简的情况下是可被证明的,而这种情况通常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抽象,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说这样的理念至少部分反映了现实世界的某些本质。例如,从微积分的观点出发,我们有连续可导的光滑存在,这实际上是我们对现实世界的一种普遍认识(也就是Wittgenstein所说的框架),因为世界中的很多事物确实都是近似光滑连续的,比如迎面吹来的风并不会离散地变大变小,热水的温度会平滑地降低而不是骤升骤降。当然,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量子化的,所以微积分的世界并不能精准建模我们的现实世界,但它在“足够多的时候足够用了”,我们可以认为它“真实”地反映了我们所在世界的某些本质。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程看常识实在论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其荒谬之处:常识反而最容易成为欺骗大脑的光影的幻象,对常识的反思恰恰带来对事物(或常识)本质的思考。例如,常识下的太阳光是白色的,但牛顿通过三棱镜证明阳光事实上是可分的。另一个绝佳的案例是非欧几何对平行线公理的改写,并建立起全新的自洽的数学工具和逻辑体系。Putnam和巴门尼德存在论的观点也存在缺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触及这样抽象的“存在”。例如,红外线和紫外线是人眼不可见的,我们无法想象出它们的颜色,但赫歇尔通过温度计侧面证明了两种“光线”的存在,延拓了我们对光的定义。理性是可以驱使我们做出超越自身感官的认识的。
换言之,理性驱使我们对世界有更深刻的思考,鞭策我们不流于对世界trivial的观察,而是探究其non-trivial的本质。我们对某件事情越“优化”,越表明我们触及这件事的本质。例如,PD-1抑制剂能够更显著地促进免疫系统对肿瘤细胞的杀伤,这就证明PD-1代表的免疫抑制是更贴近“肿瘤发生”这一背后本质的变化,而其他用于“灌水”的所谓靶点,可能并非对肿瘤发生发展最精要的概括。通过抑制PD-1我们能很好地控制肿瘤的发生发展,而早期的肿瘤杀伤药物(比如紫杉醇)通过抑制细胞分裂,事实上会影响许多其他正常生长的组织细胞,这表明相较早期的研究,今天的我们能够更精准地把握专属于肿瘤的变化,也即更贴近肿瘤的本质。后继的“靶向治疗”则表明相较“泛癌”我们能更贴近某种单一肿瘤,乃至某种基因突变亚型的本质。我们在Computing System里能看到对这一问题更简明扼要地描述,即Amdahl定律:对系统的优化应先从系统瓶颈开始。
不幸的是,数学哲学体系是有上限的。Godel通过他的不完备性定理说明了数学哲学的脆弱和局限:在自洽的系统中,总有一些命题是我们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而我们在证实或证伪任何命题之前,都不知道它是否可被证实或证伪。另一方面,物理哲学体系也为纯粹的理性哲学宣判了死刑:测不准原理表明任意时刻我们无法精准度量系统的全部状态,混沌系统理论表明,初始时刻任何的度量误差在极短时间内都可以被无限累积和放大。也就是说,对未来的预测是从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这实际上引入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逻辑,或理性,在事实上是有边界的,而这个世界是充满谜团,不可预测的。如果把我们自身当成一个Turing Machine,一旦开动,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在或近或远的未来停机,还是会是无穷地运转下去,直至永恒。尽管理性带着我们一路走过光怪陆离的感知世界,穿越怀疑虚无的泥途荒滩,直至今天构建了如此璀璨而辉煌的文明,但我们知道,就像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一样,理性也有自己的边界。
黑格尔说,否定之否定乃是事物发展曲折与必然的辩证统一。理性一路狂飙猛进的时候,最深刻的非理性也暗中滋长。而最纯粹的理性,必然孕育最癫狂的幻想。缸中之脑就是理性的边界,也是怀疑论者的终焉之问:这一切的根基,是纯粹的现实,抑或是纯粹的幻觉?这是理性永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指向理性自身:它正是脱胎于理性框架下的非理性问题。怀疑论者真正狡诈的地方在于,他只肯定理性,但驳斥理性的一切上层建筑和一切地基,让理性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把理性孤立起来,因此你无法从理性上肯定或否定它。你无法动用你的双手、双眼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正是理性斩断了你的双手,为你揭示了世界的幻影,怀疑论者要面对的恰恰是这样一个被斩断了一切的缸中之脑。可以说,这副鱼缸就是理性为自身打造的宫殿,亦是它亲自埋葬它自己的棺椁。
在我看来,与其驳斥一个永不可能被驳倒的命题,不如和它和解。除非像先辈一样引入非理性的上帝、经验、乃至框架,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用理性消解缸中之脑的疑问。但用有限的理性,去换取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是一个远比无限理性加上无限怀疑、无限欺诈和无限不可知更乐观的图景。这个世界就是存在一些命题,我们既不能证明为真,也不能证明为假,这是理性命定的悲哀;而要消解这些命题,唯一的办法是消解理性。恰恰是这些问题,说明了何种命题或思想是理性的,何种是非理性的。我们承认,缸中之脑的怀疑论是有效的,但缸中之脑的怀疑并不能打消存在的可能和存在的价值。在我看来,许多不可知论者、怀疑论者、虚无主义者的终极之问是不可被回答的,这些对生命本身意义的拷问,是不能被生命本身回答的。我们只能追求理性边界内的生命意义,无论这种感受是虚幻的还是真实的,而脱离这个层面的意义是不能在现世获得解答的。对生命意义的困惑和不可知,恰恰指向生命本身,鞭策生命在短暂的时间里去寻找存在的意义,搜集生命存在的证据。生命的意义无法在生命里获得答案,并不能说明生命本身没有意义。也许,在一个超验的世界里,上帝真的存在;而在末日审判到来之时,每一个曾经活过的生命都应该在上帝面前像尤利西斯·凯撒那样说:我来,我看,我征服。
这种观点当然是非理性的,甚至可以说是感性的。因为我们找不到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们情愿去相信这个问题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答案。但这恰好是非理性的浪漫主义肆意狂飙闪现人性光辉的时刻:即使我只有残缺的头脑,残缺的感官,即使我只是一颗苇草,我仍然要挑战我所知的未知的无垠的宇宙。
人生值不值得活,可能注定在人生中找寻不到正确答案的,只能用本能去猜测。但生命生生不息,死亡亦不可阻挡。正因世界上存在如此之多的谜团,所以无论我们是一个真实的自我还是一副鱼缸里的大脑,都应该用力地思考,用力地活着。